这篇是我们“翻书党人”的月课,刊于我的腾讯【大家】专栏。
我在《一个翻书党人的年度小结2012》中就已经提到过这本书,1111项目的读者在之前就已经读到我这篇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寻找1111位读者,进行中]。
兴于包容、毁于榨取
——评Why Nations Fail?
李华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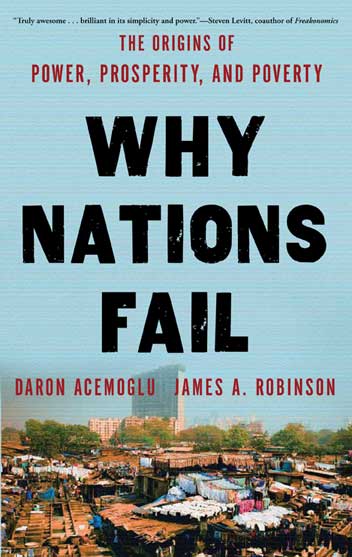
1老问题、旧答案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讨论过导致国富国穷的各种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偏僻、不接海洋没有港口、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等,会限制国家走向繁荣之路;又例如文化上民族不够勤奋、具有劣根性、没有新教伦理、缺乏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等,也会成为国家发展之路的障碍;再例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知、短视、不知道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等,也可能致使一个国家陷于贫困无法发展。
尽管地理、文化、领袖均会对国家强盛与否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呢?或者说,有没有导致国家兴衰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要回答的问题。不同于对地理、文化和领袖等因素的强调,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着眼于不同“制度”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一些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制度则正相反,阻碍了经济发展。
“制度”这一答案并不新颖。但在经济学分工日益精细的21世纪,已经很难读到像这样充满雄心和企图的作品了。目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些朝“曲径通幽处”发展的苗头,利用田野实验做发不发帐篷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或者一档循环播放的电台节目对苏丹地区教育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之类。而《国家为何失败》则完全不同,可能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经济学界重新回到宏大格局讲述国家兴衰的最有诚意的作品。不同于斯密论证的专业分工、市场扩展、自由贸易带来经济繁荣,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则讨论了“分工、市场和贸易”这些市场机制要起作用的制度基础,这“制度”一词,正是本书的关键所在。
2兴于放、毁于收
为了引出制度问题,这本大气磅礴的作品先从“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说起。人民走上广场所谓何事?还不是因为活得贫苦憋屈,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过上更好的生活。以埃及为例,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2%,且有20%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问题恰在于这个制度。埃及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并不愿意改变现存的体制,以适应大众的诉求。最终埃及只能通过革命形式来进行制度变更,这代价不低,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举。而美国人民相对富裕,主要是因为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比较宽泛,政府的可问责性较好、对选民负责,而且人们能利用各种经济机会发家致富。
纵观这些古老文明国度,比如埃及、印度与中国,为什么埃及经济增长不如印度,而印度又不如中国呢?回到惯常讨论过的地理、文化和领袖,或许可以解释部分各国发展的差异。但问题也恰在于这三个因素无法全然回答在南北诺嘉乐(Nogales)地区的差异。诺嘉乐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实行的当然是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属于索诺拉(Sonora)州,却是墨西哥的领地,实行墨西哥制度。
两个地方南北接壤,地理位置没什么不同,文化差异也不大,都是那一群人,鉴于每年大量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事实,似乎也表明墨西哥人也知道怎么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很难想象墨西哥的领导人会不清楚那些普适的经济发展原则。所以地理、文化和领袖这几个因素都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南北诺嘉乐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也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之前的理论需要修正。
两人发现南北诺嘉乐地区最不相同的是“制度”。美式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保护私人产权、实施法治、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且市场运行得到国家支持、市场向新的企业开放、市场上的个体遵守契约、并且人们可以获得教育和普遍的致富机会。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在政治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允许广泛的公民及其团体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家有制度性的问责和约束、依法行政、而联邦政府有一定的集权来有效实施法律。这种制度被作者称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与此相对的是“榨取性制度”(exclusive institution)。此处我译成榨取性制度,并没有直接对应exclusive“排外的、排斥的”的意思,而是根据全书的意思,统治者不仅不愿意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榨取大众,与民争利。
那么为什么美国实行了包容性制度,而墨西哥及其他部分拉美地区不仅没有采用类似的制度,反而实行了榨取性制度呢?这种制度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北美和南美在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殖民者实施不同的殖民策略而形成的。能否有效激励土著和新移民为经济发展而努力,成为了制度选择过程中的重要差异,尽管这种制度差异一开始非常小,但经过不断演化,其结果却大相径庭。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北美和拉美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收入差距。
关于殖民政策导致不同发展的想法,源于2001年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掀起了学界长达十年的争议,而三人姓名的首写字母也被缩成“AJR”,现在已经成了学界闻之动容的标记。从数据、史实、假设、逻辑等各个层面,大量学者卷入了与AJR的论证。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这本新书,也可以看作是对长期争论的一个总结和回应。当然顺带也承担着向大众普及新知的任务。就此书而言,相比于回应学术争论,普及工作显然做得更出色一些。
当然这种因为一线之隔导致巨大经济差距的地区还可以找到不少实例,例如现在的南北韩、例如30年前的香港和深圳。当然细究起来,尽管这些区域地理位置差不多,文化习俗也差不多,毕竟都是同一文化群体的人,但领袖的作用却极为不同。更不用说实行的制度有巨大的差异了。因此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书中,其实未能仔细处理领袖的角色问题。
他们反驳的是领导者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采用“包容性制度”的论断,但实际上,如同科斯和王宁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有可能是因为领导者面临现实的约束所致,例如“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结构,使得中国的改革不得已呈现出了“渐进改革”的趋势。仔细来看,邓小平对改革的看法,实际上相当激进,却被保守的陈云抑制,如此有了妥协之后的渐进。而领导人的能力不同,将会极大影响组织乃至国家的绩效。只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没有深入探究领导力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一个遗憾。
也就是说,除了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仔细对待地理位置、文化差异以及领袖角色。当然坊间也有误解,认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完全否认了地理、文化和领袖的差异造成不同的经济结果。我的阅读体会是,两人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无法完全解释类似诺嘉乐地区这样的问题。尽管放宽视野来看,西伯利亚的落后和美国的强盛很难说与地理位置无关,同样也无法否认历史上基督教地区相对快速的发展,更不能否认领袖的作用了。所以两人仅是指出,上述三种因素可能只能解释相对较少部分的经济成长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作用。这一点被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批评的戴蒙德倒是挺清楚,他在回应中除了强调地理因素不可忽视之外,也承认制度或许可以解释国家兴衰的大部分成因。
3盛与否、准何在
但是国家盛衰的标准是不是就等同于经济增长呢?人均GDP、贫富差距、人均寿命、乃至更综合性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到底什么才是衡量国家盛衰的标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处理,显然比较直接和简单,那就是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为国家兴衰的标准。
这种标准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衡量,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发展无非就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各种组合,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增长。而制度则是让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配置,得到优化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起来又并不是简单同意这些传统的看法,而是借用了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和企业家创新的一些观点,例如在阐释包容性制度的细节时,两人特别强调法律体系对产权的保护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家创新,从而推动生产和贸易,以及经济增长。
不过更重要的批评是这一经济增长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作为目的,那么必然遭遇哲学界关于“意义”的责难;如果经济增长本身仅仅是手段,那么增长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幸福,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我在2007年的《文景》杂志曾经发表《追求幸福的经济学》一文,其中提到经济学上的一项测算,大体而言,有一个人均收入的限制,当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时,人均收入的继续增加对幸福感提高的影响很小;但如果人均收入低于15000美元,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有有极为正面的影响。
但幸福又是什么呢?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经济学家而言,更有自嘲性质的笑话称10个经济学家能就同一个问题提供11个答案。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很难想象浙江大学校长会和舟山市金塘岛上的一个渔民对幸福会有相同的定义。而且即便两人的幸福感相同,也无法从中得出什么教益。
有一个标准或许值得考虑,那就是选择项增多,或者说选择空间扩大。尽管个人的选择能力不同,但面对更多的选择,依旧可以增进个人的效用。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人的自由的扩展。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就将发展的目标定为人的自由的扩展。收入增长与选择集扩大之间一些联系,但有些自由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增加就自动获得,尤其是政治上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但也没有细致讨论经济增长本身对制度演化的影响。尤其是“包容性制度”本身蕴含了很多价值性目标,例如自由。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自由的扩展,而自由本身又是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弗里德曼的经典论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通过自由的手段来达成。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国家盛衰评价标准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那么对于本书的论述,可能就会略觉肤浅。如同大部分政治学家在对待经济学家的工作时,一贯表现出来的不屑一样。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有值得夸夸其谈的政治学家们学习的细致论证。
4增长路、大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对此书的一种误读是“制度决定论”,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均不重要。实际上是都很重要,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未能解释在三者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何经济增长会出现重大的差异,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制度使然。
实际上,地理、文化和领袖不可能尽然相同。这或许可以反过来部分解释为什么采用了不同制度的国家,有时候也会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长。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恰好和“中国模式”的争议有关。中国的制度很难说符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设想的“包容性制度”,实际上,更接近“榨取性制度”,政治上无竞争少参与、经济上政府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但矛盾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是世界领先的。那么中国是一个例外吗?这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论述构成了挑战吗?不管怎么说,中国问题的确是两人需要认真对待的。
但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不否认存在政治权力垄断并且中央集权的条件下,稍微提升法治水平、提高产权保护的强度、并且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是这种情况下的取得的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有本质的区别。
两位作者以苏联为例,解释了这种依靠将农民和土地集中起来的做法固然能在表面上刺激经济增长,但也会发生大饥荒。与此同时,这种集体农庄的做法不仅不能激励农民,也无法在技术不进步的条件下,持续维持既定的生产水平。因为那些像奴隶一样的农民吃不饱的情况下,边际生产力必然下降。而几个五年计划并没有大幅度改进民用生产技术,尽管军事上苏联取得了长足进展。
苏联的增长,尤其是从1930年到1960年间长达三十年年均约6%的国民收入增长,迷惑了不少经济学家。著名的萨缪尔森其在1961年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预测苏联国民收入将在1984年超过美国。甚至到了1980年版的《经济学》中依旧声称苏联将在2002年超过美国。但很快柏林墙倒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谓“休克疗法”让俄罗斯经济长期处于低谷之中。
那么苏联因何失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采用的解释和哈耶克的解释如出一辙:允许私人自己做决定并通过市场来交易对社会来说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计划经济在短期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个人的激励问题,大锅饭造成人人搭便车的现象;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问题,已经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就难了。而这两个问题也恰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谓的“榨取性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也正是由于中国和苏联模式的相似性,两位作者大胆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但既然如此,何以有时候“榨取性制度”依旧会被采用,并且持续不短的时间呢?理由是榨取性制度能使经济增长中的收益不仅满足一小撮统治者的需求,并且统治者还可以有足够的资源来镇压反对者。也就是说,凡榨取性制度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集权。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不是能促进增长,关键在于能不能促进“可持续增长”。对两位作者而言,榨取性制度之所以不可能促进可持续增长,不仅是因为无法革新技术从而导致创造性破坏,更是因为搞不对制度所辖范围内参与者的激励问题。中国的增长无法持续,概因如此。除非中国的制度能从“榨取性”转向“包容性”,从而搞对激励,方能实现进一步的可持续增长。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能,其机制又是什么?一种制度从历史中走来,逐渐演化,会遇到一些“关键点”(critical juncture)。这些关键点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革命或殖民。但关键点的演变也并非全由历史决定,同样有情境因素。早期的“包容性制度”可能来自社会冲突和制度偏移。
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津津乐道的还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催生了更包容的经济制度,按照两人的解释,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实际上,这个解释也有一点“历史源头思乡症”的意思。在分析英国光荣革命这一重要关键点的时候,初期的制度偏移被认为是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的,其中重要的关键点是1492年大西洋贸易导致经济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强有力的联盟,最终导致了专制主义的终结。而与此相对的是西班牙,允许君主垄断殖民地和大西洋贸易,结果导致君主拥有大量财富和政治力量,自此与英国分道扬镳。作者还解释了东欧和西欧的发展分歧,在黑死病之后,西欧地主和封建主的势力消退,但在东欧却截然相反,从而使得东欧在16世纪重新陷入奴隶制。这一切AJ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关于制度变革的文章《欧洲的崛起》中有详细解释。
作者后续的工作还包括利用同一框架分析拉美的演化,并解释南北拉丁美洲的不同发展和落差;分析中国和日本,并解释日本何以在终结专制之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要一直到文革后才逐渐开放经济;以及分析美国南北部的不同,南方种植园主倾向于维持权力继续使用黑奴的选择,最终导致南北战争,后续一系列政治权力在社会中更广泛的分布才促成了美国的包容性增长。一开始微小的制度差异最终导致的经济结果完全不同。这样听起来,还是有些历史宿命论的色彩。但作者认为不可不必如此“悲观”。实际上从“榨取性”到“包容性”的制度转型是可以达成的,只是这或许需要一次“政治革命”,例如美国南北战争。
5改制度、不革命
要依靠革命才能完成的制度转型,听起来依旧不是个值得乐观的选择,尤其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对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会不会发生革命,都有很大的争议。尽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简单回顾了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历史,但两人对中国制度转型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细致的。
就中国的长期增长而言,地大物博当然是个优势,而且东部城市一直人口众多,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儒家传统中既有推崇诚信有利交往的一面,同样有尊崇等级不利分权的一面,单纯将儒家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有过度简化的嫌疑。只是目前并没有看到上佳的经济史实证研究来估计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化挤占了儒家文化的存在空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更是打断了文化传承。尽管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是有意无意利用了传统儒家文化来维系社会稳定,但也仅限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与儒家有所关联。
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人历经更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显然没有如科斯和王宁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那样细致处理“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垄结构,而仅仅是大体认定邓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当然,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确变得更为包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释放了大量的人力及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加上有限度的产权保护、鼓励投资,从而造成了中国的快速增长。
但正如福山对此书的批评一样,两位作者在处理“包容性”与“榨取性”制度这样的概念时,不够细致。而且与道格拉斯·诺思、约翰·瓦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在《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一书中提出的“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和“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相比,也没有新意。在诺思等人的论述中,有限准入秩序也是由于一小撮精英联手打造一个腐败利益集团,设租寻租贪腐受贿,同时限制大众享有的政治经济上的好处,限制他们进入获得权益的机会。不难看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言的“榨取性制度”与此相差无几。
这些概念或许有点太宏大了,以至于很难进行精确定义,也无法顾及其中细节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例如两位作者对中国的“榨取性制度”表示悲观,但这样一种简化的概括并不足以展示中国的动态。除了上面谈及的领导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外,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没有解释“榨取性制度”如果放宽一定程度,允许更多准入,甚至朝“包容性制度”略有转向,这个过程释放出来的制度潜力是不是足以支撑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
与苏联的榨取性制度不同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做到了分权,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财权去中心化了。钱颖一、巴里·温加斯特以及诺兰等还发展了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并解释了政治上的适度集权以及经济分权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好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了在“包容性制度”里需要一个强大的能控制腐败的中央政府,而这一点安德烈·施莱佛早在其一系列研究中论述过了。这样一个听起来继续要一定集权又需要大量分权的包容性制度,很像是中国目前的制度,但作者们认为中国的制度是一个榨取性制度。
当然,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既有包容性的方面,也有榨取性的方面,要探究的是制度的内部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之间是否可以兼容。而恰恰是这“兼容性”落在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视野之外。例如尽管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俄罗斯胜于中国,但据透明国际的统计,俄罗斯的腐败程度高于中国,且经济增长也慢于中国。国际社会现在喜欢把中印两国放在一起比较,尽管地理和文化截然不同,而且虽然说人口数量有一比,但人口结构又完全不同。尽管印度的政治体制很包容,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却远逊于中国,经济增长同样慢于中国。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可以辩称这是因为时段不够长的缘故,拉长时段来看,情况可能会不同。但对于现实的决策者而言,制度转型就是要在关键点上做出重要的抉择。
政治参与增多的确使得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增强,但也有可能出现提高腐败和妨碍经济增长的例子,这个时候两位作者的补救措施是提出一个适度集权的中央来抑制腐败、平稳社会、推动增长。问题在于谁来抑制集权化的中央“利维坦”式的扩张?如果是要依靠更进一步的司法独立或民主政治,那么就又会削弱中央的集权力量。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制度背后,有太多制度选项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两位作者没有调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包容性制度内部也会出现矛盾,更没有给出当这种内部选项不兼容出现时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恰是中国问题的挑战所在。
中国似乎永远是个谜。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他们只能断言中国的失败。但正如福山诘难的那样,中国是可能失败,但如果是200年后呢?也许值得探究的是中国已经发生的制度变迁,经济上的包容性制度改革已经探讨较多了,而政治上,至少相较于毛时代,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范围和程度都有了提高。这至少说明政治制度朝“包容性”的方向迈了一小碎步,尽管不足以使整个制度转成包容性,但也足以激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了。人们期待的当然是中国的平稳转型,而不是革命。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谈及这个选项,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定无法持续,概因不革命就无法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但对于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人来说,“如何能不革命又完成制度转型”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幼稚地期待唯一确定的答案,每一个人都将展开自己的思考,这才是重点。这也是一本好书带给读者的最大收益。正如我之前给“政见”网站推荐本书时说的那样:一本好书或许不在于取得一致的赞扬,而是在一群聪明人中引发争议。当然鉴于自己愚笨,或许要再加一句:一本好书不仅引发聪明人的争议,而且能给蠢人也带来教益。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
继续【寻找1111位读者,进行中】欢迎转播。
可以选择是否包含以下声明:
觉得文章有用?认为作者靠谱?立即  支付宝支付1元,支持作者!
支付宝支付1元,支持作者!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